栏目分类
热点资讯
一位代孕妈妈口述: 生一个8万元, 三胞胎最值钱
发布日期:2025-07-05 18:02 点击次数:121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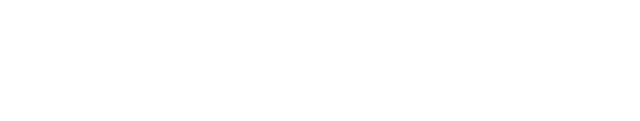

采访、撰文|元枝
编辑|灯灯、野格
十点人物志原创
今年五月,一则“长沙县一非法代孕别墅被查处”的新闻,再次引发了公众对于非法代孕的关注。
据报道,别墅内部设有手术室、实验室和多个病房,每天有多辆无牌车将女性运送至别墅进行代孕或取卵,平均一天有4-10位女性在这里接受手术,其中还包括聋哑女性。
虽然我国早在2001年就将代孕列为违法行为,但这条黑色产业链却从未真正消失,甚至有女性为了赚取高价酬劳铤而走险,主动成为代孕母亲。
然而,代孕的代价,远比人们想象中更残酷。那些看似天价的报酬,最终换来的往往是健康和尊严的彻底崩塌,有人幻想着代孕几次以后就好好生活,却永远地留在了冰冷的手术台上。
我在工作中认识的一位朋友名叫莱雅,是个缅甸女孩。偶然的机会下,我得知她曾被迫成为一名代孕妈妈。她平静地告诉我:“代孕害死了我妹妹,也毁了我的一辈子。”
东南亚素来有“代孕工厂”之称,在缅甸、泰国、老挝等国家,代孕团伙猖獗。九年前,莱雅和妹妹敏丽被送至东南亚某处代孕基地,被迫成为代孕妈妈。六年时间里,莱雅和敏丽共代孕了13个孩子,亲身经历了从花季少女沦为生育机器的全过程。
莱雅说,代孕从来不是简单的“借腹生子”。它是赤裸裸的生命交易,而代孕妈妈,则是这场生意里,最卑微、最无助的牺牲品。
以下根据莱雅的讲述整理。

家乡,悲剧的开始
我叫莱雅,今年29岁。
我出生于缅甸克钦邦的一个小村落,那是个不见天日的地方,充斥着贫穷和战乱,我们的生活就像一滩死水,永远在为温饱发愁。枪声、炮声和惨叫声伴随着我们长大,人们早已习以为常。
在我的家乡,教育是奢侈品,女孩从出生起就背负着繁重的劳动任务,被无形的牢笼所束缚。幸运的话,一个女孩从出生,到成年,再到暮年,都不会迈出村庄一步,这已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结局。

缅甸克钦邦,图源视觉中国
在我十六岁,妹妹敏丽十三岁的时候,我们还在玉米地里和Meh-Meh(妈妈)忙农活。
那是很寻常的一天,黄昏的阳光渐渐消退,一点点余晖红得像血,我们饿着肚子,满身的草屑,热浪在眼前翻滚。
妈妈那时才三十岁出头。她十五岁生下我,明明很年轻,但是在我的印象中,她好像一直那么苍老单薄,佝偻的身躯在夕阳下投下了长长的影子,粗糙的双手和土地一个颜色,指甲里总是嵌着泥土。
妹妹敏丽坐在我旁边微微笑着,她只有十三岁,天真又胆小,我非常疼爱她。
虽然我从小就知道,这里的女性,一生注定是悲剧,但没想到,这天来临得那么快。
我们的父亲是个矮小又丑陋的男人,我不知道他是做什么行当的,但我见过他毒瘾发作的样子,见过他手里拿着刀,一脸阴狠的样子。他不是好人,我们所有人都知道。
三个陌生的男人跟着父亲,他们眼神冷漠,步伐沉重。看见这些陌生人,我心里突然涌上一股不安的预感。
父亲没有和我们打招呼,而是直接走向母亲,低声说了些什么。我无法听清他说了什么,但我看见母亲原本带笑的眼睛突然瞪大,嘴唇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,我知道她在恐惧。
下一秒,母亲用双手紧紧抓住我们,将我们往身后藏。她单薄的背影在四个男人面前显得格外无助,她和他们无声地对峙着。
父亲转过头指着我和敏丽,眼神里没有一丝愧疚和温情。他说:“那是我的两个女儿,你们带走吧。”
我愣住了,却没有特别意外。我见过太多女孩前一天还在和我们玩耍,第二天却不见了踪迹,村里的人会说她们去了“好地方”。
妈妈紧紧抓住我和敏丽的手,不想让我和妹妹被带走,却被气恼的父亲踹到一边。她跪在父亲面前,扯着他的裤子祈求:“卖我吧,求你了,别卖我的孩子。”
“快点带走她们。”父亲的话犹如死刑宣判,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我看着父亲冷漠的脸,他常挂在口中的那句“等你们长大了,我就把你们卖了”原来不是玩笑,我们不过是他的一笔财产,能够随意买卖。
母亲尖叫着,向来软弱的她死死扯住我和妹妹的手臂,指甲深深划入我的皮肉,却被暴戾的父亲用铁棍打断了手臂。
我惊恐地看见母亲手臂错位变形,她痛苦地在地上尖叫着,但棍棒依然无情地落在她身上。
我扑过去,狠狠咬住父亲的胳膊,却被他一棍子敲破了头。周边围了几个村民,他们窃窃私语着,“卖两个女儿,发财喽!”
那三个男人粗暴地把我和妹妹拉进一辆破旧的卡车。卡车的车厢里已经挤满了女孩,空气中弥漫着人体的酸臭味。
卡车开动,我看见妈妈拖着变形的胳膊,踉踉跄跄地追在车后面。她的鼻子、嘴巴满是鲜血,撕心裂肺地喊着我和敏丽的名字——这是我们母女三人的最后一面。
敏丽的眼中充满了恐惧,小声喊着:“姐姐,我怕……”我和敏丽紧紧相依在一起,努力让对方感到一丝温暖。敏丽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,她的泪水浸湿了我的肩头。
车厢内一片死寂,偶尔响起女孩们的哭泣声。车子开始颠簸,像是一只没有方向的船,带我们驶向未知的深渊。

丧失人权的八年
最初的两年,我们被拘禁在一片破棚屋里,做卖淫女。
红灯区的生活让人痛不欲生。这里每天都有新的女孩被送来,也有女孩消失。女孩被客人殴打、虐待是常态,女孩们的惨叫就像头顶的乌云,时时刻刻笼罩着我们。
我和敏丽不是没想过逃跑,但我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,又被切断了一切和外界联系的方式,尤其是看到试图逃跑的女孩被抓回来,受尽惨绝人寰的酷刑后,我们就再也不敢起这样的心思。
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,我一定要活着,这样才能回家见到妈妈。

缅甸仰光,图源视觉中国
我18岁那年,老板突然将我们聚在一起,说:“现在有个工作机会,可以让你们得到身份证明和钱,你们到时候想去哪就去哪,这笔钱足够让你们过上好的生活。”
那时候我们都不明白“代孕”的具体含义,还以为只是照顾小孩。我们被集体拉去做了体检,合格的只有寥寥几人,其中就有我和敏丽。我和敏丽当时多开心啊,终于能够逃离这个满是虐待和血腥的地方了!
我们再次坐上卡车,全程被蒙住眼睛,戴着头套,兴奋地奔向了并不善待我们的命运。
这一次,我们依然被关在某个无法知晓具体位置的基地,荒芜、破旧、四面环山,但是居住环境好了很多,有了像样的房间能够遮风避雨,而不是像红灯区那样,只有摇摇欲坠的棚板和一块布帘。
管事的人知道我和敏丽是亲姐妹后,好心地让我们两人单独住一间宿舍,这里的伙食也比红灯区好多了,每顿饭甚至有牛肉和牛奶。
我们一来就被打了促卵针,过了十几天,我被送到一个陌生的诊所。我记得自己躺在肮脏冰冷的手术台上,长针从我的身体里穿过,我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(后来才知道是取卵),但是剧痛让我惨叫不止,手术过后,我甚至站都站不起来,之后我得到了一小叠钱,说是给我的辛苦费。

图源BBC纪录片《代孕者》
我高兴地把疼痛抛在了脑后,把那一小叠钱折了又折,放进贴近胸口的内衣里,生怕把它弄丢了。
敏丽才十五岁,因为年纪太小,加上长期营养不良,这里的“上司”让她暂时先做清洁工和食堂工的工作。晚上她干完活回来,还给我带了肉汤,好奇地问我今天去干了什么?
我把钱从内衣里掏出来,一张一张摆在床上,看着敏丽眼里越来越亮的光,我俩开心地笑了,当时的我们真的对未来充满希望……
起初,我们每天吃好吃的饭菜,集体运动和玩耍。半年后,我跟敏丽都胖了一些,除了营养增加了之外,更多是因为取卵导致的浮肿。虽然每个月的促卵、取卵让我无比恐惧,但至少不挨饿,不挨打。我和敏丽渐渐对这里产生了“家”的感觉,也通过一个清洁工阿姨学会了简单的中文。

图源BBC纪录片《代孕者》
清洁工阿姨告诉我们,我们运气好,进了高端公司,服务的是有钱的客人,要是运气不好进了黑作坊,这辈子也不会有自由。据说,黑作坊里的女人会被打断手脚,绑起来生孩子,一个接一个地生,连恢复时间都没有,生不了就被卖掉做小姐,服务有怪癖的客人,榨干她们最后的价值。
基地也有“老师”每天给我们描绘未来的美好生活,举例因为代孕发家致富的“成功女性”,甚至用照片证明她说的话是真的。我和敏丽越发对这里产生依赖感和信任感,一度天真地以为,做代孕妈妈或许没有那么可怕。
基地里的代孕妈妈们大多来自缅甸、柬埔寨和老挝。许多女性和我们一样,是没有身份的黑户,被卖来或者骗来基地。也有一些女性是本地人,通过中介介绍来这里赚钱,能够自由来去。
“上司”告诉我们,要想买身份,重获自由,需要40万人民币,而生一个孩子能挣8万人民币。将养了半年,我和妹妹的身体达到了怀孕的指标,我兴奋地想着,自由指日可待了!

代孕妈妈,命如草芥
怀孕后,我和一些孕妇也熟悉了起来,我会问她们“生孩子疼不疼”、“孕妇每天要干什么”等问题,大家也会友善地回答我,当时我感觉,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。
但是没多久,这个天真的幻想就破灭了。基地里有一个代号“17”的女孩,我认识她的时候,她已经快临盆了。“17”那时候才23岁,来这里四年,却已经生了六个孩子,为了多赚钱,她每次代孕的都是双胞胎,代孕期间流产过两次。
“17”说,她来这里是因为自己的孩子生病了,她必须多赚钱,回去给孩子治病。每次赚来的钱,她都会拜托和她交好的工作人员寄回去。
“17”说到家人时,眼睛总是亮亮的。但是家里没有电话,她也不会写字,她常念叨,不知道现在孩子过得怎么样,身体有没有恢复?
然而,没过多久,“17”就在生产时死在了产床上。和她同产房的代孕妈妈说,“我躺在床上,余光看见17号躺的那张床,鲜血顺着被子滴在了地上,她生的两个孩子哭得好大声,一听就很健康”。

图源BBC纪录片《代孕者》
有人问,“17”生孩子的那些钱怎么办?和我们相熟的阿姨说:“这个女人太笨了,她都不知道,她每次寄的钱都被她那个所谓的朋友私吞了,朋友给她的票据就是购物小票,反正她也看不懂,她家的孩子估计早没了”。
突然有个年轻的女孩哭了起来,陆陆续续的,越来越多人哭出了声,也不知道是在为“17”而哭,还是为自己哭。
我代孕的前几个月还算平静,我感到身体逐渐适应了这个新生命。然而,到第六个月时,我出现了严重的妊娠反应,剧烈的孕吐让我的健康状况直线下降。到第八个月时,我几乎消瘦到无法下床,肚子却巨大无比,每天都伴随着剧烈的呕吐,我没被红灯区的痛苦打倒,却差点因为孕吐而轻生,我甚至故意摔跤,想要摔掉这个孩子,但是没有成功。
这里生产时没有麻醉,也不能做剖腹产手术,必须是顺产。我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那种痛,我因为疼痛叫出声,却被医生扇耳光怒斥,我甚至能听到医生用剪刀剪开我下体的声音,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把孩子生下来的,等到我恢复意识的时候,身边已经没有了孩子的踪影。

图源BBC纪录片《代孕者》
那一刻,我彻底领悟到,我究竟身处一个怎样的人间炼狱。然而,我没有时间悲伤,我在休养了六个月之后,又要进行下一轮怀孕和生产。
敏丽的状况比我糟糕。敏丽的第一次代孕失败了,第二次不到半个月便流产,第三次成功怀孕,但怀到第四个月时,又流产了。
基地很生气,想要把敏丽卖掉,我别无他法,只能接受多胎代孕,为敏丽争取到了四个月的休养时间。
这次是三胞胎,每个人都说我活不下来了,基地几乎没有人生三胞胎。但我想活啊,我的愿望仅仅就是活着而已。可能是看我可怜,也可能是多胞胎的雇主出了高价,我生产的时候,医生很专业,甚至有个温柔的护士在旁边安慰我,孩子很顺利地生了出来。
我是基地第一个成功生下三胞胎的人。或许这真是一个大单,基地甚至给我提高了每个孩子的价钱,一个孩子十万,还给了我八个月的休养时间。
我只能麻木地告诉自己,再忍忍。
敏丽在第四次尝试后,总算成功怀孕,十个月后生下孩子。老天保佑,这胎她没受什么罪,甚至都没怎么疼就把孩子生下来了。我以为是敏丽身体好,后来才知道,她这种情况属于急产,非常惊险,一不小心就会大出血。
在代孕基地,我见过很多产妇在极度痛苦中去世,也见过为了救婴儿被活剖的代孕妈妈。有些人前一天还在和我说话,第二天却再也不能问出一句“你今天还好吗?”很多代孕妈妈生完孩子,仅仅是咳嗽了一声,人就没了。
敏丽生最后一胎的时候大出血,基地不准备救她,我们两个残破的身体靠在一起,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我从来没有这么平静过,就好像每次分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,对于死亡已经不再害怕了。我只是在她耳边说:“敏丽别怕,你死了姐姐就去陪你。”

敏丽和莱雅依偎在一起
我也不知道她是怎样撑下来的,但是她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。
六年里,我生了七个孩子,一次三胞胎,一次双胞胎,两次单胎;敏丽生了六个孩子,两次双胞胎,两次单胎。
那几年我常常在想,我们这样的人,还算是人吗?而那些孩子呢,到底算什么?
我没读过什么书,但我觉得有一个词很适合用来形容这些孩子——“罪证”。

重新开始,何其艰难
2019年,我24岁,敏丽21岁。
用十三个孩子和残破的身体,我们终于买到了梦寐以求的自由。六年前,我们被蒙着眼睛送来这里,六年后,我们又被蒙着眼睛送走。
像我们这样被卖过来的黑户中,很多人攒够了钱,买了身份,好不容易出去了,没多久却又重新回来代孕。我曾经很看不起她们,等到自己出去后,才终于理解她们的无奈。我们和社会脱节太久了,重新融入人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离开前,和我们交好的清洁工阿姨给我和敏丽一人戴上了一条红色的手绳,祝福我们以后平平安安,一生顺遂。她还叮嘱我们,出去后最好找中国人或华裔的店工作,可能薪水不会很高,但是一定会很安心。阿姨的妈妈是泰籍华人,因此阿姨的中文很流畅。我和敏丽跟她学了六年中文,日常对话完全够用。
出去后,我们又花了一大笔钱找中介买工作,加上各种零零碎碎的打点,这些年在代孕基地挣的钱已经所剩无几。中介介绍我们去泰国曼谷的一家高端会所做泰式按摩技师,我和敏丽很高兴,因为我们迫切地想拥有一技之长,靠手艺赚钱。

敏丽第一次在泰国玩时拍下的照片
会所的管理人员大多都是中国人,听说大股东也是一个中国人。在同事们的帮助下,我们很快适应了这里的新生活。
那段时间是我们人生中少有的安宁时光。同事们特别友好,总是给我和敏丽分享水果和零食,有时候忙到忘了吃饭,也会有同事给我们打包一份快餐。公司聚餐团建去泡汤,看到我们身上的生产痕迹,同事们没有人刨根问底,为我们保留了体面。经理周姐还常常搂着我和敏丽的肩膀说,“这是我的两个妹妹,中文说的比我还好”。
同事们的好,令我们受宠若惊。我和敏丽愈发努力地工作,成了店里月月上榜的优秀员工。
2023年3月,在周姐的推荐下,我们来到中国交流学习。临别时,周姐说,等我们学习回来,就给我们升职。

莱雅姐妹第一次在中国下馆子
正当我们以为终于苦尽甘来的时候,命运再一次给了我们重重一击。这年11月,敏丽开始频繁感到腹痛,她一天比一天虚弱,体重持续下降。敏丽的身体状况引起了周姐的重视,她安排人陪敏丽去医院检查,结果,医生告诉我们一个噩耗:敏丽被确诊为卵巢癌晚期。
敏丽开始接受抗癌治疗,但治疗费用高昂。为了筹集治疗费,在周姐的帮助下,我们去了深圳的高级会所,以特聘技师的身份工作,工资翻了一倍,同时公司也出于人道主义,给敏丽补偿了整整8万元,周姐还在私底下给我转了2万元,让我带着妹妹治病。

莱雅排长队给敏丽拿检查报告
我拼了命地工作、存钱,希望能让敏丽活下去,但敏丽的病情却在不断恶化。听到医生说敏丽以前的代孕经历可能是造成癌症的关键原因后,我无力地跌坐在了地上。
那天,当我又一次看到医院的女厕所门上印着代孕信息时,我终于崩溃了。我在厕所里发疯,想把那些东西抠下来,抠到指甲鲜血直流,忍不住放声大哭。

医院凳子上的代孕广告
最后的日子里,敏丽一直在流血,极度痛苦,我甚至不敢碰她,一碰她就疼到昏厥。她总是问我,“姐姐,我可以出去吗?我不想被关着了”。我只能骗她,“医生说你下周就好了,等等吧”。
一周又一周,敏丽瘦成了一把柴,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:“姐姐,你说当年妈妈的手到底好了没有啊?我有点想她了……”2025年2月14日,敏丽在泰国去世。
敏丽去世时,我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。周姐抱着我说:“敏丽这么好的姑娘,下辈子会幸福的,你好好的,她肯定想看你好好地活下去。”
每个人都劝我好好活下去,日子还很长,伤痛总有过去的那天。但我无法释怀,每当想起敏丽天真的笑脸,想起我们那八年在红灯区和代孕基地遭受的折磨,巨大的悲伤、愤怒、痛苦就快要把我吞没。
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看见这个故事,但希望看见的女孩们记住,代孕母亲没有人权,不要让身体成为商品,生命被践踏。愿我们的悲剧不再上演。

结语
讲述过去的遭遇时,莱雅大部分时候都很平静,只有提起妹妹敏丽时,她的眼泪会止不住地流。
莱雅曾说,敏丽的死带走了她生的希望。完成采访的几个月后,我们再也无法联系上她。据周姐说,莱雅已主动辞职,离开了公司,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。
但愿莱雅只是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疗愈自己。

敏丽的红绳断了
部分配图源于受访者。
